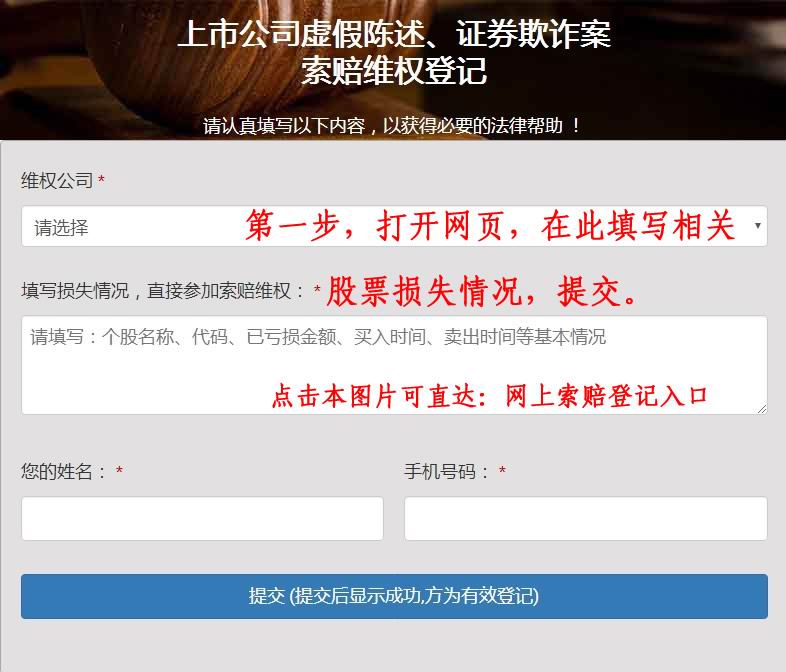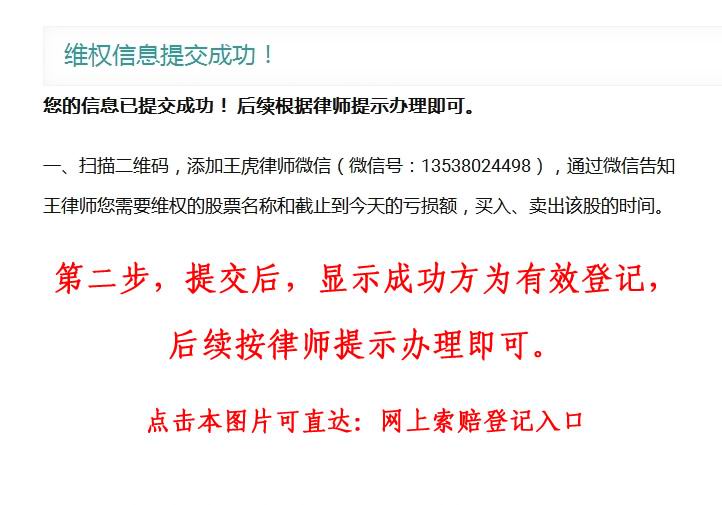正文
一
虚假陈述的认定
(一)虚假陈述定义及类型
《虚假陈述若干问题规定》第4条针对虚假陈述作出界定,即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在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虚假陈述。
根据前述规定及司法解释的其他内容,实践中,针对证券虚假陈述可根据不同的标准作不同的分类:
从虚假陈述对市场和投资行为的影响角度,虚假陈述可区分为诱多型及诱空型虚假陈述两种类型。诱多型虚假陈述,指的是故意发布虚假利多信息或者隐瞒利空信息,使得投资者在股价高位时继续投资追涨买入,并最终遭受不必要的额外损失。诱空型虚假陈述,指的是发布虚假利空信息,隐瞒利好信息,是的投资者在股价低位时消极卖出股票,并遭受损失。
从行为表现来看,虚假陈述的种类可区分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的类型,具体如下:
(二)虚假陈述的“重大性”
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领域,以“重大性”作为限制或者豁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独特要件,只有信息披露的内容具备“重大性”特征,行为人才需承担相应的侵权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规定,侵权行为(虚假陈述内容)不具有重大性时,行为人不负赔偿责任。
“重大性”,指的是违法行为对投资者决定的可能影响,其主要衡量指标可以通过虚假陈述违法行为对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影响来判断。
至于“重大性”特征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虚假陈述若干问题规定》第10条第1款前两项列举了推定具有重大性的情形,但同时,该条第2款规定,如被告提交证据足以证明虚假陈述并未导致相关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明显变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内容不具有重大性。
从司法判决来看,重大性特征是认定虚假陈述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的前提,因此,在个案当中,案涉虚假陈述是否具备“重大性”往往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亦同样为法院事实认定的关键。从司法案例来看,法院认定虚假陈述是否具备重大性特征,需要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认定:
第一、从结果层面,需审查证券交易价格及交易量是否发生明显变化。例如,在(2022)甘民终499号民事判决显示,针对虚假陈述是否具备重大性,法院从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及交易量来看,结合“三日一价”交易量及股价显示,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并不足以导致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发生明显变化。法院最终判决驳回投资者的诉讼请求。又如,在 (2024)赣01民初110号案例中,针对虚假陈述是否具备重大性问题,法院亦从实施日、揭露日证券交易量及交易价格角度进行分析。法院认为,该公司所作虚假陈述为诱多型虚假陈述,实施日后并未导致股价明显上涨,甚至出现下跌的相反情况,在揭露日及其后,除揭露日当天股价下跌1.76%外,次日起连续十个交易日涨跌额累计13.77%,因此认定虚假陈述揭露并未导致股票交易价格及交易量发生明显变化,进而认定该公司虚假陈述的内容不具有重大性,驳回投资者赔偿请求。
第二、如出现股票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发生明显变化的,则需进一步分析认定该等变化的原因是否系由虚假陈述所导致。例如,(2024)新01民初号民事判决显示,虽然在虚假陈述揭露日后,该上市公司股价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但法院认定该等下滑系因为上市公司集中发布的其他重大利空信息、上市公司经营风险等造成,而非由虚假陈述引起,并据此认定原告诉请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具有重大性。
二
因果关系认定
传统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侵权行为、过错、损失及因果关系。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领域,因果关系区分为交易因果关系及损失因果关系两个独特的方面。
(一) 交易因果关系认定-推定因果关系
交易因果关系,指的是因为虚假陈述行为而引起投资者作出证券交易,交易因果关系为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前提。
在传统民事侵权责任领域,因果关系的要件需由原告方进行举证,考虑到证券赔偿领域的特殊性,我国证券虚假陈述领域民事赔偿纠纷适用的是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即:只要投资者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更正日期间实施对应的证券买卖交易(即在诱多型虚假陈述买入证券,在诱空型虚假陈述中卖出证券),即推定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与虚假陈述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前述推定允许被告举证推翻,如被告能够举证证明投资者交易行为与虚假陈述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则无需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例如,在(2024)赣01民初110号民事判决中,法院对投资者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的证券交易原因分别开展分析认定:
针对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后买入股票的交易,因法院已经认定某科技公司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进而认定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后买入股票的行为与某科技公司虚假陈述之间不存在交易因果关系。
针对投资者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的2021年8月25日卖出13,000股股票的交易行为,因为该公司已经在2021年8月17日发布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的提示性公告,法院认为,该破产重整信息系导致股票交易价格及交易量明显变化的关键因素,并认为,该等出售股票行为系受到公司其他重大事件影响,进而认定投资者出售股票的行为与虚假陈述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
该案判决最终以不存在交易因果关系为由判决驳回投资者损失赔偿的诉讼请求。
(二) 损失因果关系认定
损失因果关系,指的是投资者因受到虚假陈述影响进行证券交易而遭受的损失。《虚假陈述若干问题规定》第31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查明虚假陈述与原告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导致原告损失的其他原因等案件事实,确定赔偿责任范围。该条第2款规定,针对原告的损失的影响因素,被告可以进行举证,如能够证明原告损失部分或者全部系因其他因素(例如,他人操纵证券市场、证券市场的风险、证券市场对特定事件的过度反应、上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等)而非虚假陈述引起的,可相应减轻或者免除赔偿责任。
例如,在(2022)甘民终499号民事判决中,针对投资者损失的影响因素,法院认为,从两股股指跌幅可以看出,恒康医疗股票下跌叠加了股灾的因素,相比之下恒康医疗股价跌幅远小于沪深两市跌幅,可以认定投资者的损失系股灾引发的证券市场的风险,股票复牌后补跌导致,因此,投资者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并判决驳回投资者的诉讼请求。
又如,在(2022)鲁民终2368号民事判决中,针对投资者损失中应当剔除的因素,法院认为,考虑到虚假陈述涉案时间较长,在此期间证券市场走势波动较大,投资者的损失中部分损失系系统性风险造成,应当剔除。
三
投资者损失认定
(一)损失范围认定
《虚假陈述若干问题规定》第25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原告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原告实际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
该司法解释第27条及第28条分别规定了诱多型虚假陈述及诱空型虚假陈述所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计算方式。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股票交易的数量及频次等因素导致投资差额损失较为难以计算,法院倾向于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测算,例如,不少案例显示,法院委托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对投资差额损失进行专业测算,并据此认定投资者的实际损失。
(二)不计入损失的范围
因证券市场股票交易量及交易价格的波动除受到虚假陈述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多方因素的影响,为此,《虚假陈述若干问题规定》第31条亦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裁判时应当对原告遭受损失的原因进行查明,并将除虚假陈述以外的原因导致的损失剔除在外。
该条第2款规定,被告可对引起原告损失的其他因素进行举证,如举证成立的,可相应减轻或者免除自身的赔偿责任。
从司法案例来看,在证券虚假陈述赔偿纠纷案件中,较为常见的的事由包括:
1、系统性风险因素
系统风险是指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化、汇率波动等对证券市场产生普遍影响的市场风险,属企业实体之外的因素,对该类风险个别企业实体无法控制,投资者也无法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
从司法案例来看,在投资者损失交由专业机构(中证法律服务中心)进行测算的情况下,该机构所测算的损失已将系统性风险因素考虑在内,并相应扣除系统性风险因素所造成的投资者损失。
2、非系统风险因素
非系统风险,指除证券市场系统风险以外的其他风险,其主要表现为上市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导致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的商业风险。因非系统风险需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进行认定,因此,从司法案例来看,如果委托中证法律服务中心进行损失测算的,其所采测算一般并未扣除非系统风险,因此,是否扣除非系统风险以及扣除比例问题,亦为原被告双方庭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人民法院结合具体案情认定。
例如,在(2023)甘01民初178号案例中,法院认为,股票投资既有的风险、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经历了重大事项停牌、收购海外资产失败等一系列提示性公告,该等因素均对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的额整体股价走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某公司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叠加效应,共同导致并加剧了股价下跌。法院酌定投资者损失中应予以扣除的非系统风险比例为80%。
又如,在(2024)辽01民初572号案例中,法院结合公司所处行业趋势变化及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等因素,酌情认定,在扣除系统性风险后,非系统性风险因素导致投资者损失的比例为10%。
再如,在(2024)粤民终635-675号民事判决中,因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上市公司既披露影响股价上涨的利好消息,也披露了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冻结、被动减持的利空消息,法院酌情认定投资者扣减系统风险后10%的损失属于非系统性风险引起,而予以扣除。
四
常见责任主体及责任范围认定
(1) 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人、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过错责任
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第78条针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体范围进行进一步扩展,在原《证券法》所规定的发行人、上市公司基础上进行修改,规定发行人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均承担信息披露的义务,具体包括:
发行人,包括证券发行时的发行人以及发行证券后的发行人(上市公司);
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重大资产重组、再融资、重大交易有关各方等自然人、单位及其相关人员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
根据《证券法》第85条“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承担的责任形式属于无过错责任。
(2)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过错推定责任
《证券法》第85条规定,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由此可见,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担的为过错推定责任,如需在证券虚假陈述诉讼中免责的,则需对自身不存在过错进行举证,否则,即推定其具有过错并应与发行人共同承担责任。例如,在(2023)甘01民初178号民事判决中,因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组织且参与涉案虚假陈述的实施,法院认为,徐某刚为实际控制人,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且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并判令实际控制人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3)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过错推定责任
《证券法》第85条规定,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虚假陈述若干问题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主张对虚假陈述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其工作岗位和职责、在信息披露资料的形成和发布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取得和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为核验相关信息所采取的措施等实际情况进行审查认定。
根据《证券法》、《虚假陈述若干问题规定》的前述规定,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承担的责任形式属于过错推定责任,在诉讼中,该等主体应对在信息披露中已经尽到勤勉尽责义务进行举证,否则,即依法推定其未尽到勤勉尽责义务,对发行人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具有过错,并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证券法》第85条规定的董事、监事等应承担连带责任,但并未明确限定连带责任的范围,从司法案例来看,人民法院在认定该等主体责任范围时,倾向于根据过错程度判令其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参考案例:
(4) 证券服务机构(审计机构)的责任承担-过错推定责任
《证券法》第163条规定,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及其他鉴证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文件由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虚假陈述若干问题规定》第18条针对证券服务机构过错认定的标准予以明确,即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参考行业执业规范并结合服务机构核查、验证底稿等相关证据,认定服务机构是否存在过错。
从现有司法案例来看,在众多的证券服务机构中,承担发行人财务审计职责的审计机构因出具的审计报告行为而被投资者起诉要求承担责任较为常见,因此,本文着重选取对涉及审计机构责任认定及承担的案例。
在 (2022)黑民终1290号民事判决中。中某会计师事务所为某上市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后经法院查明并认定,在该年度内,公司下属的红博商贸城在年度报告中未确认应支付七建公司应支付工程款2.91亿元,延期付款利息及仲裁费0.98亿元,导致影响公司2016年度净利润0.98亿元,导致公司净利润降低至-0.61亿元。作为审计机构的中某事务所对工大高新公司2016年财务审计时取得了和解协议及应付利息计算表,但未发现公司少计提利息9688.64万元、仲裁费88.81万元的重大错报,并据此被财政部作出行政处罚。
针对投资者要求审计机构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法院认为,该审计机构对于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重大、异常情况,未按照执业准则、规则,审慎、勤勉地执行审计程序,未举证证明自身不存在过错,并酌情判令审计机构在5%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其他参考案例: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梳理可以看出,虽然《证券法》规定具有过错的证券服务机构在虚假陈述案件中应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但人民法院在具体个案当中,往往会结合服务机构的过错程度进而将其连带责任限制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
结语
本文通过对司法案例的深入分析,探讨了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中的多个核心问题,包括虚假陈述的界定、重大性的认定、因果关系的认定、投资者损失的计算以及责任主体的责任范围。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虚假陈述若干问题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指导,但每个案例的具体情况都有所不同,需要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进行细致的判断。这些案例不仅为法律实务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为投资者权益保护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希望本文的梳理能够为相关各方在处理证券虚假陈述案件时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帮助。
注释
【1】法律推定的情形包括:
(1)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事件;
(2)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要求披露的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
(3)虚假陈述的实施、揭露或者更正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产生明显的变化。
【2】《虚假陈述若干问题规定》列举的可用于推翻交易因果关系的情形包括:
“(二)原告在交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虚假陈述,或者虚假陈述已经被证券市场广泛知悉;(三)原告的交易行为是受到虚假陈述实施后发生的上市公司的收购、重大资产重组等其他重大事件的影响;(四)原告的交易行为构成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证券违法行为的;”
【3】一是风险评估程序,二是测试被审计单位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制度,三是执行收入测试时注重运用分析程序,四是针对收入实施检查程序。
武
【版权声明】:图文转载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之用,禁止用于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联系。
围下,真正做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